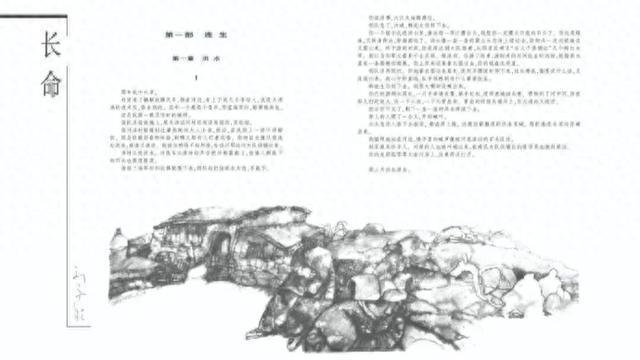

从20世纪90年代初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横空出世至今,刘亮程已走过30多年文学发表的历程(创作的历程应该更长)。这过程反复证明他确实能不断给人惊喜,不断超越自我,又始终忠实于自我,是一位广大读者信得过的优秀作家。
刘亮程创作道路从“村庄”开始,从打上了刘亮程鲜明印记的关于一个新疆普通村庄的全套知识开始,或者用他本人的话来说,“我全部的学识是我对一个村庄的见识”。其实每个作家(每个人)的生命都只能从某个“村庄”或广义的地方开始。刘亮程的特点是一直固守“村庄”。但他的固守决非抱残守缺,而是不断反省、回味、挖掘、拓展,由此不断丰富和提升他关于“村庄”(虚构的“黄沙梁”“碗底泉”或现实中故乡新疆沙湾县)的各种知识。他迄今为止的写作,就是不断改写其关于“村庄”(关于中国某个“地方”)的知识。

刘亮程
跟许多读者一样,我也很早就震惊于他的“元气之作”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。许多来自乡土生活经验、充满灵气和哲思的清辞丽句汩汩而出,让我很自然地想起当时正巧再度走红中国读书界的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亨利·戴维·梭罗。我还曾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和张炜《融入野地》、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、毕飞宇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放在一起,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美文与灵性之作。
但我也不无疑虑。我不知道(或者说担心)从如此罕见的起点开始,刘亮程还能走多远?他能走到“村庄”以外别的“地方”吗?若他去了别的地方,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再回到“村庄”?他在空间上将如何触达“村庄”以外的无数对应物?比如外地?城市?家族?国族?世界?当然我也好奇,他将如何展开“时代”“历史”“过去”“未来”这些任何类型的文学都无法回避的流动性时间概念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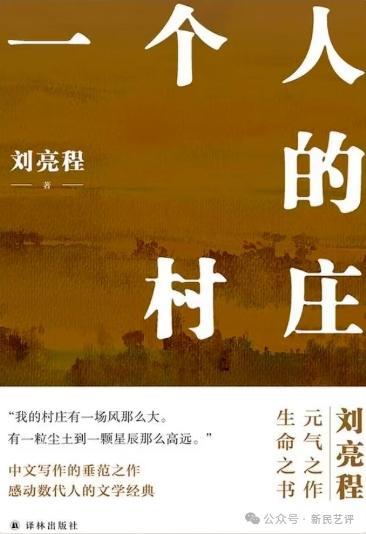
很惭愧我并非研究刘亮程的专家,但有限的跟踪、关注、浏览告诉我,他的创作似乎也正是在一步步努力解答上述问题。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之后的散文集《大地上的家乡》,以及小说《虚土》《凿空》《捎话》《本巴》,包括最新的长篇《长命》,不仅频频走出“村庄”,走到外地,走向大大小小的城市,走向家族、国族、世界这些似乎绝对凌驾于“村庄”之上的宏大概念。他也努力超越时间的阻隔,走向过去和未来,甚至向死亡发起正面强攻,使人鬼杂处,幽明相通,在改写村庄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写中国文学关于生与死的知识。
在不断拓展的时空框架中,刘亮程不仅写“人”,也写了包围人(或与人共处)的整个世界,写世界上各种颜色、气味、声音,写风、土、动植物甚至高天、神鬼与魂魄。他不仅“贴到人物来写”,更贴着天地来写。他不仅讲人的故事,也讲神鬼魂魄的故事。他呈现给读者的不再只是写人的书,更是他蓄谋已久、也曾反复预告的“见鬼之作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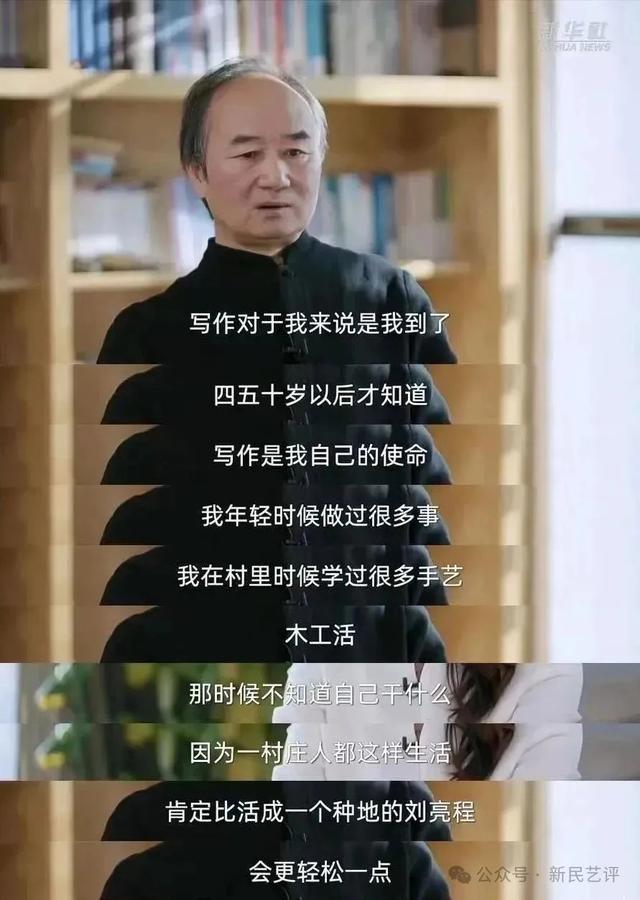
之所以这样写,他自己说是想取消人在文学上仿佛不证自明的绝对中心地位。他的作品犹如“村庄”戏台上的戏曲,首先唱给鬼神听。人只是旁观者,偶尔也听到一些,分享一点。但这种说法更像是刘亮程擅长的修辞和话术,需要作一些必要的“翻译”。毋宁说这三十多年,刘亮程不断从“村庄”走向“村庄”以外无数的地方,也从“人”走向“人”之外无数的他者。但他总不会忘记丈量现当代中国人生存的广度、深度与高度,亦即人的存在复杂多元的可能性。
《长命》写家族历史,写族谱(包括那些仅仅起过名字却并未出生的家族成员),写死者的游魂与生者不断对话,写生者的魂梦以及特有的精神状态(比如“恐症”)如何向着悠长的家族和村庄的历史敞开——所有这些都是借助文学来拉长个体暨群体的生命,以照见人的存在的丰富内涵。

这一切刘亮程究竟做得怎样?大家不妨从各个角度来探讨。但有一点很清楚,三十多年来刘亮程很幸运没有丢失其罕见的元气、灵气与才气,但他又并不满足、并不完全依赖其天赋的元气、灵气与才气。他向外国文学、古代文学、民间文学、现当代文学学习了许多,所以他每部作品的写法都各不相同。他尤其向三大民族史诗《江格尔》《玛纳斯》《格萨尔王》学习了许多。他甚至把《突厥语大词典》看了好多遍。
前年参评茅盾文学奖,我也曾为《本巴》争得面红耳赤。事后回想,不禁汗颜。对《本巴》所依托的文学与文化传统,我知道多少?《长命》思考生命的短暂与绵长,其文化和宗教背景,我相信许多读者也不甚了然。所以更重要的还是要向作家刘亮程学习,不仅学习他创作的文本,也学习其创作所依托的丰富的所学。
原标题:《新民艺评|郜元宝:从“村庄”走到“村庄”以外——评刘亮程《长命》及其他》
栏目编辑:李纬 文字编辑:江妍
来源:作者:郜元宝
(文化责编:拓荒牛
 )
)









 晋ICP备17002471号-6
晋ICP备17002471号-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