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大众对于“七夕”的印象,变成了“中国人的情人节”这个概念,很商业化。其实若说是“中国人的情人节”,元宵节应该更匹配,但商家们无所谓,节日促进消费,总是越多越好了。
七夕也称“七巧节”,这个节日由来已久,最重要的,就是传说牛郎织女在这一天鹊桥相会。最早可追溯到《诗经》:“跂彼织女,终日七襄……睆彼牵牛,不以服箱。”此时的牛郎织女还只是天上的星宿。
到了汉代,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基本成型并广为流传。《古诗十九首》说: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。纤纤出素手,扎扎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,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,相去复几许。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。”
我小时在浙西衢州的乡村生活,每到七夕,老人家也会讲到牛郎织女的故事。老人年年讲,孩子们年年听,也并不厌倦。这个爱情故事华美又凄凉,隐藏着人生的不完美,容易让每一个凡人带入自己的情感而掬一把同情的泪,因此得以流传千年。
每年的七月初七,牛郎织女见面,一年只这一次,这次见面的情况,自然备受大家的关注。到了这一个晚上,人人都举头望天,看那银河,银河皎皎兮,鹊桥可搭成?河汉迢迢兮,桥梁都坚固。
牛郎织女一年一次见面,这次见面要做些什么、聊些什么,也令人有无尽的想象。
牛郎会老吗?应该不会变老,否则再怎么相见。两个人见面应该有无尽的话语要聊,聊聊庄稼与收成,聊聊牛马与羊群。织女,作为天上的神仙,也并不那么自由,想起来,也跟我们凡夫俗子差不多,没什么意思。牛郎呢,虽然是个平凡人,没有什么才华,却给人提供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与可能性,会不会有一天,也有一个天仙落入凡间,成为自己的爱人?
就这样,坐在稀薄的月光下的凡夫俗子,把思绪拉远,拉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天上人在相会,地下人在想象。当然,也要做点什么。比如家家户户都把庭院清扫干净,少女们向织女星虔诚跪拜,乞求织女保佑自己心灵手巧,像个仙女一样;也希望因为自己有智慧,有巧手,而觅得良人。
南宋周密著《武林旧事》,记录杭州杂事,其中提到“乞巧”,说“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,发发杯盘,饮酒为乐,谓之‘乞巧’;及以小蜘蛛储盒内,以候结网之疏密,为得巧之多少。”
乞巧的方式,各有不同,更像是一种游戏。《清嘉录》上也载:“七日前夕,以杯盛鸳鸯水,掬和露中庭。天明日出晒之,徐俟水膜生面。各拈小针,投之使浮,因视水底针影之所似,以验智鲁,谓之‘发巧’。”
老杭州人高诵芬(1918-2005)出身于杭州的世家望族,高家曾为“高半城”,说杭州有半个城的产业都是她家的。她于1994年移居澳大利亚后,与其子徐家祯共同创作回忆录《山居杂忆》,记录了很多杭州旧时风俗,其中也写到了“七夕”的风俗——
“……每家都要供香烛。我母亲说,织女手巧,会做花织布,所以女孩子应该祈祷织女保佑,以后长大了也能成为巧手。于是晚上也在天井里供上香烛和水果四盆,叫我跪拜,再用清水一大碗,供到次晨,见水上会结起一层皮。此时将缝衣针一根,轻轻投到水面,针便会停在水面而不会沉入水中。据说,水面的针在碗底投下阴影,如果影子呈一根细针状,那么女孩子长大之后会成巧手;如果影子是粗粗的一根,那么女孩子长大会是笨蛋无疑。”
人们对于牛郎和织女,历来都是同情为多,也知道这一对情人一年相见一次,自然是忙乱得很,世人怎敢忍心打扰他们——“多情欲话经年别,哪有工夫送巧来!”
丰子恺也在随笔里写到“七夕”,收在《缘缘堂随笔》里,“我家姊妹多,祭双星时,大家在眉月光中穿针,穿进者为乞得巧。我这男孩子也来效颦,天孙总是不肯给巧。这些虽是迷信的玩意儿,回想起来甚有趣味。古人云:‘不为无益之事,何以遣有涯之生?’”
七夕的夜晚,在平淡的乡村生活里,是浪漫的神来之笔。人们在上弦月的微光里,把思绪寄托到遥远的地方,把祝福交付给遥远的对象,而隐约的祝福,其实也送给自己。
顺便也要提一笔,在《清嘉录》中还有《看天河》的记载,“七夕后,看天河显晦,卜米价之低昂,谓晦则米贵,显则米贱。”老百姓生存不易,米价之贵贱也要看老天的颜色,这一下子又把神仙的日子拉低到人间的凡俗里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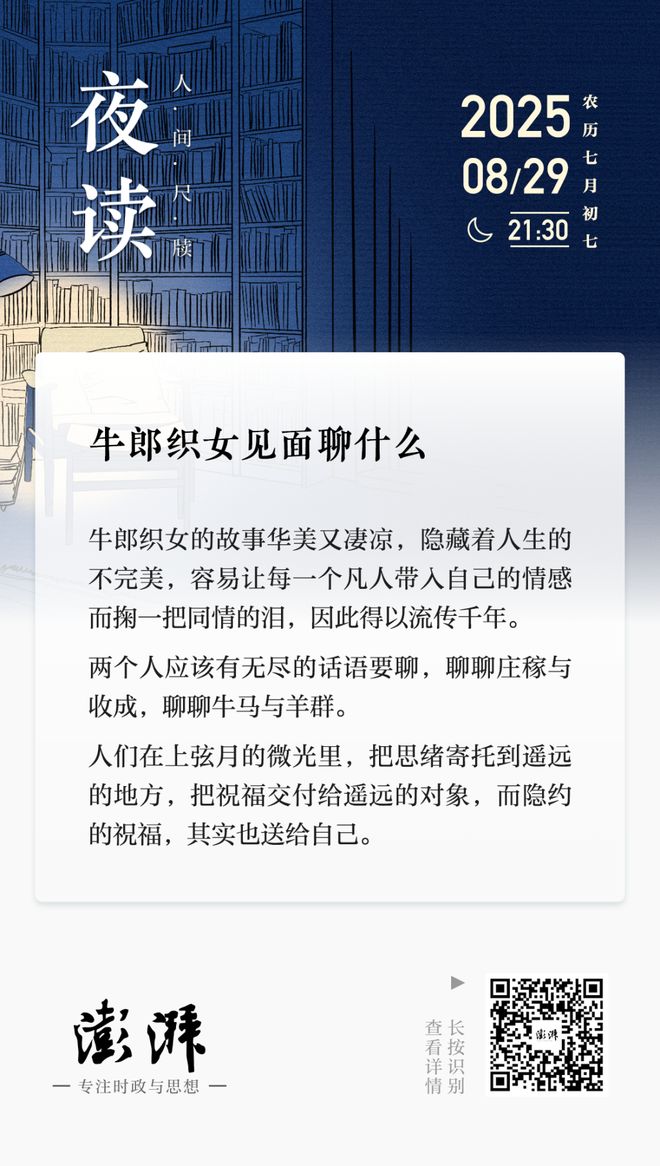
(文化责编:拓荒牛
 )
)









 晋ICP备17002471号-6
晋ICP备17002471号-6